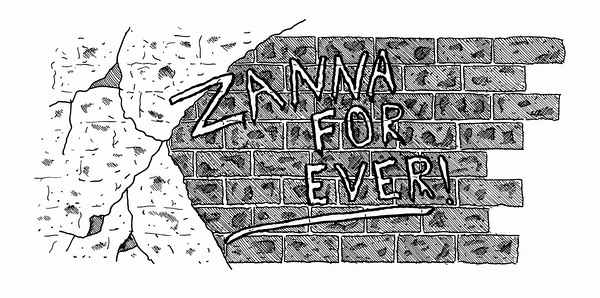接下来一上午,札娜一直躲着朋友。排队领午餐时她们终于再次相逢,她却没好气地赶她们走,大伙儿只好顺着她。
“算了,”凯思说,“她大概心情不好。”
“是糟透了吧。”贝克丝说,说完大家便大摇大摆离开,只有狄芭留下。
她没开口跟札娜说话,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她。
下午放学时,狄芭特意等着札娜。札娜本来打算直接冲出去,却还是被狄芭逮个正着。她一把挽住札娜的手臂,札娜佯装生气,撑不了多久便宣告破功。
“噢,狄芭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她说。
她们走回一起居住的社区,往狄芭家走去。狄芭家人的热情健谈虽然有时不免吵闹又无厘头得令人抓狂,但大致来说很适合当作任何讨论的背景音效。一如往常,街上的人直盯着这两个人看,因为她们看起来是很逗趣的组合:狄芭比她纤瘦的朋友矮胖,仪容不整,没扎马尾,一头乌溜溜的长发就这么随意披散。札娜却总是把一头金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。她一路沉默,狄芭则叽里呱啦地问她有没有事。
“哈啰,瑞宣小姐。哈啰,慕恩小姐,”两个人走进门时,狄芭的爸爸从沙发上轻快地招呼着,“刚刚都在干吗?小姐们要喝杯茶吗?”
“亲爱的,”狄芭的妈妈说,“今天过得好吗?札娜,你呢?”
“瑞宣先生、太太好。”札娜说。她和往常一样,对着在沙发上向她微笑的狄芭父母挤出一抹既局促又高兴的笑容。“我很好,谢谢。”
“别吵她啦,爸。”狄芭一路把札娜拉进房里,“不过茶还是要的,拜托了。”
“这么说,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吗?”狄芭的妈妈问,“什么新闻都没有,你今天竟然一片空白!太令人惊讶了!”
“还好啊,”她说,“老样子嘛,对吧?”
狄芭父母赖在沙发上一搭一唱,对她每天生活总是一成不变的处境深表关怀。狄芭翻翻白眼,把门关上。
她们坐了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。狄芭涂着唇膏,札娜只是坐着。
“我们该怎么办,札娜?”狄芭终于开口,“最近怪事连连。”
“我知道,”札娜说,“真的越来越严重了。”
说不清一切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,但至少已经持续了一个月。
“记得我看到云的那次吗?”狄芭说,“那朵长得像你的云?”
“那是几个礼拜前的事,从没看过那种怪东西。”札娜说,“说说具体一点的事好了。今天那只狐狸、那个女人、墙上的东西、那封信……”
一切是从初秋开始的。那天,她们在玫瑰咖啡馆。
门开时没人特别注意,直到她们发现来人竟悄悄站到她们桌旁,她们才纷纷转头注目。
那个人身穿公车司机制服,帽檐朝气十足地向上扬起,咧嘴向她们笑着。
“抱歉打扰了,”那女子说,“希望你别……看到你本人真是太兴奋了!”她对大家微笑,但只对札娜说话,“我就想对你说这句话。”
女孩们惊讶得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。札娜还来不及挤出回应,凯思就迸出一句:“你说什么?”狄芭早就笑起来,但那女子不以为意,还说了个莫名其妙的词。
“史瓦纪!”她说,“我听说你会出现在这里,本来还不相信。”她又笑了笑,便径自离开了,留下一桌女孩不以为然地放声狂笑,直到服务生跑过来请她们控制音量。
“疯子!”
“疯子!”
“根本就是疯子!”
如果只是这样,那天的事不过是伦敦街头又一则见怪不怪的奇人诞事——但事情并非如此。
几天后,狄芭和札娜经过横越艾佛森路的旧桥下时,抬头一望,在一个高得不可能有人摸得到的鸽子窝后面,看见一片潦草涂鸦,用鲜黄色油漆写着:札娜万岁!
“天哪!大概有谁也叫札娜吧,”狄芭说,“否则就是你的手特别长,要不就是有人疯狂爱上你了,小札。”